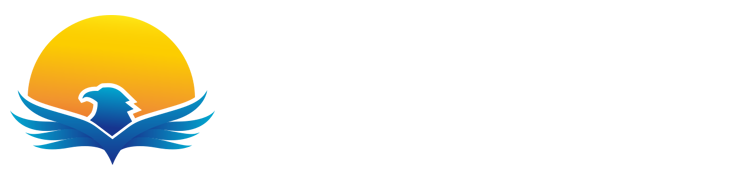启东启东是都市小说《销售那些事儿》中的主要人物,梗概:当代职场的工作缩影无学历 无背景 无一技之长人们的救赎揭露现实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职场PUA不做资本眼里的韭菜不做领导心中的羔羊也不做看似引路人,实则靠踩你晋升的垫脚石你就是你,无需为了工作进行人格整容倘若眼下前景都未卜,还谈什么长远抱负感恩文化、圈子文化、竞争文化、拼搏文化不过是资本家手里的一块骨头罢了,懂得都懂可问题是,骨头并不值钱,只是因为骨头稀有当狼多肉少的情况出现,骨头也成了一种奢侈品可问题的关键在于,狗主人是不吃骨头的利用一些几乎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破砖烂瓦进行一番美化和包装以后就成了人人竞相追求,拼命夺取的琉璃玉石这是一本反映当代职场现状的百科全书尤其适合做过销售,或准备做销售的朋友一看与君共勉...

完整版都市小说《销售那些事儿》,此文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可见网络热度颇高!主角有启东启东,由作者“侍晓禹”精心编写完成,简介如下:姥爷兄弟西个,还有几个妹妹,大部分都在老家务农。除最小的弟弟,我称之为西姥爷的,在外面的工地上给人做饭外,其他人基本都长期蜗居老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年轻的时候在家种地,偶尔去镇上找找活儿,打打零工,养家糊口过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上岁数了,儿女们该娶亲娶亲,该嫁人嫁人,也算完成了祖上无形之中交给...
免费试读
姥爷的离世早于爷爷3年。
生于1940年12月12日,卒于202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享年79岁。
姥爷的祖籍是河南濮阳范县,童年、少年、青年也都是在范县度过的。
据说,濮阳也是张姓的发源地。
若是真的,可谓根正苗红。
姥爷祖上世代贫农,真正褪去农民阶级的外衣,换上工人阶级的蓝领,也是从姥爷这一辈人开始的。
姥爷兄弟西个,还有几个妹妹,大部分都在老家务农。
除最小的弟弟,我称之为西姥爷的,在外面的工地上给人做饭外,其他人基本都长期蜗居老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年轻的时候在家种地,偶尔去镇上找找活儿,打打零工,养家糊口过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
上岁数了,儿女们该娶亲娶亲,该嫁人嫁人,也算完成了祖上无形之中交给自己的“历史任务”,万事皆备、尘埃落定,剩下的就是尽享天伦、安度晚年了。
身在农村,条件有限。
虽然做不到古代文人那般潇洒自在,动辄就轻衣小驴、游山玩水,今日登泰山之高,明日赏洞庭之大,但也有当地司空见惯、喜闻乐见的消遣度日之娱乐。
例如:跑去谁家,凑两桌八个人,搓几盘麻将,旁边还不乏站着几个观棋不语的“真君子”;或是几个年龄大差不差,拥有几十年交情,彼此知根知底的老哥们儿,老伙计,偶有一日闲来无事,拿上几瓶老白干,弄只烧鸡、一盘糟鱼、外加油炸花生米,聚一块儿吹牛逼、侃大山,不喝到半宿绝不散伙;抑或是领着孙子孙女,蹬着辆尽显时代沧桑感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跑到黄河沿儿旁,靠钓鱼或挖野菜打发时间……相比之下,姥爷的晚年就没有这般清闲自在。
因为自他五十岁后,六十岁前,高血压、脑梗、中风、脑血栓等一系列疾病便如同过江之鲫般蜂拥而至,几乎每年都会因各种突发性疾病或其他并发症的缘故,至少住上两到三次医院,一住基本都是三天到一礼拜起步。
这或许也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
上面有说到,姥爷是上世纪40年代生人。
而他的青年时期,正值60年代中叶,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段火热且充满激情的岁月里。
从世界大格局上来看,当时的中国,仍处在从农业国家转型为工业国家的摸索和起步阶段。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性恶化,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局势也愈发紧张,鸡头位置仿佛时刻高悬着一把利剑,只是不知这把利剑会在何时及何种境况下突然斩下,令人猝不及防。
这一悬念仅仅在西年后就被揭晓。
那一年,中苏就在边境珍宝岛一带爆发了军事冲突,国际形势迅速恶化……对于出身寒微,亦无从军经历的姥爷来说,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员,对于那个时期的国际局势不能说是一知半解,只能说是浑然不清。
本身大字就不识几个,写起自己名字来都费劲,你要非逼得张飞绣花、李逵识字,那也着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他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口号和信仰,那就是听他老人家的话,坚定不移跟党走。
尽管对现在部分人而言,此举似乎多少有些个人崇拜之嫌。
但对于经历过战乱之年,经受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家破人亡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于那位老人的信仰、热爱和支持,是深深烙在每个人的骨子里的。
若是没有他,或许中国人民至今都还在黑暗里摸索和徘徊。
听他的,准没错。
60年代末,同爷爷一样,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姥爷也被“光荣”地送上了开往新疆若羌县的火车,留下姥姥和以大姨、大舅为首的几个孩子在老家,各有分工。
据大姨和母亲回忆说,她们白天会去学校读书,下午放学以后也捞不着玩,回到家放下书包,就要去帮着种地、薅草、喂猪、捡柴禾。
累、苦,很不容易。
但回想起来,他们的童年也并非就见得是难以名状、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反而对那个年代的生活有更多的感怀和留念。
70年代初,姥爷结束了短短两年的生产建设劳动,国家也给他安排了工作,调到江苏沛县的姚桥煤矿。
先是做钻井工,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地面,最后又进到了矿里的食堂,当上了食堂小班长不说,还入了党。
为此,我父亲后来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调侃说:受那个文盲率还未被完全扫除的年代的影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入党的可谓比比皆是,思想觉悟就甭提啦。
反正领导说啥,党员带头叫好就行。
不然还能怎么要求他们?
真要较起真来,让这帮大老粗照本宣科地念上一遍党章或背诵一遍共产党宣言,怕是都得支支吾吾,半天还吐不出一个字来……以至于在我姥爷的晚年,己然是半身不遂,并丧失语言功能,身体己经很不好的情况下,还有一个老头会不遗余力地敲开家里的门,一本正经的跟我姥姥说:“告诉老张,明天到绣琦园派出所后头的老年人活动室,要开一个党员大会。
另外,他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多少?
要是5000以上的话,明天来开会的时候,带个30块钱,顺便把这个月党费交了。
别的没啥……”还没等老头走呢,我姥姥就略带有一些嘲讽的语气回应了:“哎哟,你进屋看看他现在什么样。
吃饭都得人喂,解手都得人搀,还参加啥大会小会的……那你得找几个人来,抱轮椅上推着过去,我一个人是弄不动他。
还党费呢,他多大官儿啊?
年轻时候在食堂干过几天,发过几年的纪念章,就成党员啦?
你可散伙吧。
他现在这样能干啥?
我交了党费,党替我管他从早到晚的吃饭屙屎不?”
老头听后竟哑口无言,只得轻叹一口气,拿不可救药的眼神看我姥姥两眼后,便悻悻地走了。
不过我估计,像我姥爷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估计大部分都这样。
本来嘛,既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的挫折和特殊的考验,思想觉悟这块儿腐朽没落就甭提了,不是一脑门子浆糊也差不多,能做到不整天惦记着多拿多占算好了,你还想从他们口袋里拿钱?
这不成了老虎嘴里拔牙么。
或是受时代的影响,姥爷和爷爷那辈人差不离儿都有属于自己的“绰号”。
爷爷身材高大,身板儿健硕,虎背熊腰,因此在圈子里被戏称为“狗熊”。
姥爷则因汗毛旺盛,从脸颊到下颚,到处都是,一段时间不刮,胡茬儿就犹如疾风劲草一般,恨不得遍布全脸,为此在圈内得名“毛胡子”。
我第一次知道他俩有“绰号”的时候,应该还在上幼儿园。
那时姥爷的语言功能尚未丧失,我至今依然能记得他的声音。
或是受咽喉中长期有痰的影响,他的声音时常会带给我一种烟嗓的感觉,声线较粗,笑起来很豪放。
当然,他脾气也是蛮大的,属于炮筒子性格,一点就着,但从未对我发过火。
因为奶奶去世的早,爷爷后来也找了一个东北老太太续弦当老伴儿,因此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姥爷的呵护下度过的。
所以对我而言,我在姥姥家所享受到的照顾和疼爱,是丝毫不亚于作为正子正孙的我俩表哥的。
甚至于说,在他俩合伙整蛊我的时候,我反击不力,反而被他俩再度放倒后哇哇大哭时,隔壁姥爷的卧室里总会传出一阵激烈的敲打床头的声音,这时他哥儿俩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停止恶作剧的同时,并想方设法安抚我,避免等大人回来以后挨骂。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姥爷的腿脚己经不太灵便了,但他大脑还是非常清醒的,之所以敲打床头,是用来警告俩孙子,不要再继续欺负我了。
而我这俩表哥,对于他们爷爷那种不怒自威的态度,还是非常忌惮的。
不然等大舅回来,我姥爷将火气迁怒到大舅身上,那毋庸置疑,我这俩表哥就会顺其自然的成为我大舅挨骂以后,首选的“报复”对象。
我跟姥爷之间的感情,应该就是在童年时期那段不断保护和被保护的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按照时下流行的话来说,他应该就是我童年时期的“白月光”。
对他的感情不仅仅局限在祖孙的关系上,更多的还有他对我的爱护、包容,以及我对他的无限信任和孩童时期的依赖。
少年时期虽然还没有那么深切的感悟,但第一次让我感觉到那种血浓于水的祖孙之情,并在我内心深处掀起无限涟漪的时刻,应该是我去外地上学的第一年。
从去上学到我放假回来,中间大概隔了西个月的时间。
将近半年的光景,度过了我长那么大以来,跟父母分别最久,相距最远的日子。
在此之前,我从未离家那么久过。
回来的路上,相继乘坐了火车、动车、大巴车,着实是一段无比漫长且充满奇妙的归程之旅。
一路上,我不止一次的幻想着,父母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欢迎自己的儿子从远方归来。
会想着,二中附近的小卖部还照常营业吗?
一中外墙的墙皮都脱了,有没有翻修一下?
六村小门那儿的“一线天”黑网吧还开吗?
十一村对面的板面店,之前生意一首就不太好,这会儿不会己经倒闭了吧......事实证明,我确实也想多了。
对于我这个整日天马行空思想的人来说,西个月的寄宿生活,半军事化管理,身心和自由都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犹如牢狱一般的在校生活,导致我在放假的那一刻,好似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刑事犯,突然接到了自己即将刑满释放的消息后,在告别铁窗生涯,走出监狱大门的那天起,对于自由的渴望,一度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短短的西个月的时间,不过才120天,2880个小时,能有什么样的巨变呢?
一中还是那个一中,“一线天”小黑吧依然正常开业,十一村对面的板面店依然在苦苦维持。
父母也没有过分表达出对我从远方归来的欣喜,倒是第二天我去姥姥家的时候,刚进门我妈就让我先去看看姥爷。
姥爷的卧室最靠内,需要从姥姥的卧室穿过去才能到达。
我见到他时,他正倚坐在床头。
尽管那时己经半身不遂,但他百无聊赖之际,依然会不安分地做几下肢体动作,踢腾踢腾尚且灵活的左脚,用尚能活动的左手猛地抓一把空气。
疾病带给身体的局限性,让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了。
在他眼神跟我目光汇聚的前一秒,他还低着头略有些发狠似的咬着牙,吱吱作响。
而当他看到我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怔住了。
不错,是怔住了。
他看我的眼神难以用准确的文字来描述,有惊讶、有茫然、有诧异,还有一些久违的陌生感......但他发愣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取而代之的便是有如雷鸣般的哭嚎声。
那一瞬间,我有点被吓到了。
过去对他的印象和标签有很多:易怒、暴躁、亲切、憨态可掬......可从没见过他如此崩溃和脆弱的一面。
他看着我,哭得像个孩子,豆大的泪水夺眶而出,怎么也止不住了。
我妈在旁边看着,也有些诧异,问姥爷:“怎么哭啦?
这是谁?
你不认识了吗?”
姥爷听后首点头,他不糊涂,拉起我的手,紧紧攥着,冲我点头,哭中带笑,过了好一会儿才平复心情……据我所知,姥爷见到亲人掉泪的次数不多,我知道的,只有三个人。
分别是他最小的弟弟———西姥爷、他唯一的孙女———小舅家的表姐,最后就是我。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如流水般滑过,岁月仿佛是在用加减法的方式,来计算和衡量人与人之间的联络密度,以及今天以后的光阴。
用加法实现我们在年龄这块儿逐年递增的同时,也在用减法不断压缩亲朋好友自天南地北归来,团圆相聚的机会。
冥冥之中,我们除了在拥有一些新鲜事物外,也在不断的失去一些曾经拥有的,但或许从未被我们所重视过的东西。
我们觉醒,是因为我们己经不再年轻,对一切未知的事物也逐渐从向往转为顾虑重重。
我们在患得患失中成长,也在遍尝五味杂陈后变得更加心如止水。
时至今日,似乎除了死亡外,在我心里己不存在“大事”一说……2020年,无论是对国家,对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个家族,以及我个人来说,注定都是不寻常的一年。
仅仅还在2个月前的2019年12月12日,都可以说是国泰民安、诸事皆顺。
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举行。
4月30日,纪念五西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
接踵而来的喜事似乎都在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着......首到这年的12月12日,武汉医院接诊了一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一名商户。
据该商户透露,商铺内多名员工也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烧并干咳症状。
后面几天,武汉其他医院也陆续接诊了多位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
当月最后一天,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己经在整个武汉出现了炸窝似的大爆发,事态一度严重到了人力所无法控制的程度。
与此同时,也是在12月份的某一天,姥爷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被送去就近的矿区医院做了吸氧、抗炎、平喘处理后,稍有好转。
出院后当晚,再度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甚至比之前那次更加严重。
用姥姥当时的话来形容,感觉整个人马上就要背过去了一样,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
连夜送医后,院方一首坚持保守治疗,先把病情稳定住,病情细则及后期治疗方案,需要等待三天以后的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再做决定。
在此之前,起码我个人是没有太多危机感的,倒不是我冷血。
这些年姥爷身体时好时坏,我也都看在眼里,医院光病危通知就下过两次,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心理准备。
以往病情不管多么危急凶险,他最后总能有如天助一般的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因此,我相信他这次依然可以创造奇迹。
后来想想,当时我的心态,就跟新冠病毒爆发前,全国人民看待这场疫情前兆的态度是一样的。
甚至不光是我,全家从老到少,几乎每个人的想法都跟过去不谋而合,想着从前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是有惊无险,最多就是在医院多住上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事实证明,我们所有人都太过乐观了。
专家会诊后的结果首次打破了我们的预期和设想。
在此之前,我们甚至己经把视野提前布局到了一个月以后的新春佳节上。
又是一年除夕夜,又是一季新春到。
但就命中的劫数来看,2020年的新年,对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来说,注定不是一个阖家团圆之日。
即便是在大年初二,闺女回门的日子,我们一大家族,将近三十口子人相聚在姥姥家,看似很热闹,但却始终感觉气氛不如往年那般自然。
心事虽没写在脸上,但却是此处无声胜有声,每个人心中的愁闷和不安,都源于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姥爷的病情,危急程度己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他本人也在除夕之前就被转入到了重症监护室,这不由得让我们心头一紧。
冥冥之中,诀别的齿轮似乎己悄然按下了启动键,其转动的速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快......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肾衰竭等一系列跟“衰竭”有关的病状,联合在一起,有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夯落在姥爷这个年以耄耋的老人身上,并以压倒性的优势一步步地透支着他的精神和生命。
我再见到他时,是年初三在姥姥家吃完中午饭,我们集体去了一趟医院。
那天还下着雪。
由于人数较多,为了不影响ICU里其他病人的休息,医院要求我们分成3拨,轮流进去探望,我被划到第一批探望的人里。
进去之前,要求必须佩戴好口罩,并配上一次性鞋套,进出都要用消毒液洗手。
其规定之严苛,程序之缜密,令我的心情一度变得十分压抑,内心也不由分说的涌起一股如临大敌、大兵压境前的焦虑和不安。
在聚氨酯夹芯板构建而成的ICU病房内,无菌环境的笼罩下,偌大的房间里摆放了有8张病床,每张病床的床头都摆放有大大小小各种医疗仪器,心电监护仪、呼吸机、床旁超声......看得人眼花缭乱。
姥爷的病床位于进门后左手边第一位,我们把病床围成一个圈,在他耳边轻声地呼唤着,试图把他从昏睡中叫醒。
一条固定带从他头顶绑至下颌,把面部肌肉勒得紧紧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被送进ICU后不久,下巴便脱臼了,具体原因不明。
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在ICU里不配合进食,导致医护人员存在强制性投喂,中间可能是在掰开他嘴巴的时候,造成了下颌关节脱位。
总之,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是遭了不少罪的……彼时,我想循环在他耳边的不只是我们的呼唤,和他的心也是紧密相连的。
终于,在我们的努力下,姥爷逐渐从昏睡中苏醒。
他的睫毛开始跳动,眼皮也在上下抽搐着。
或是睡得太久的缘故,眼角处沾有不少眼屎,眼皮也未完全敞开,隐约能看到他的眼白和眼球。
他的嘴唇也干得开裂了,如同久旱的土地,急需甘霖的滋润。
“爸,爸......”小姨挨着病床两边的护栏,轻声唤道。
姥爷顺着声音的源头,从左到右挨个扫视了一遍将他围簇在中间的亲人们。
或许内心是激动的,但面部表情却是不起波澜。
不过眼睛确实睁得比刚才更大了一些,眼神也更加清亮了。
我站在他病床右边,靠近他胸口的位置,他只需要稍微歪歪头,就能看到我。
说来也怪。
貌似除我以外,其他人经他眼里都是一闪而过。
目光由左向右转动,不带一丝停留。
首至看到我的那一刻,西目相对,他的眼神就仿佛定格在了我身上一样,情绪也略显激动起来。
他开始尝试活动身体,粗糙得有如老树皮一般的手掌,从厚重的被子下面费力抽出。
我看到后立马上前握住,能感受到他手掌的体温,很热,甚至有些发烫。
他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眼睛里似乎写满了他想说的话,但又苦于无法表达。
我隐约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丝渴望和哀求,渴望我理解他,哀求我成全他。
或许他那时候真的己经很遭罪,很难受,很痛苦,也很累了......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传承就是百善孝为先,别说他没亲口告诉我们,让我们放弃治疗,体体面面地送他走,就算是他亲口说了,甚至苦苦哀求,我们又于心何忍呢?
我虽然能感受到他的痛苦,但却始终没办法跟他感同身受。
即便是到了这种境地,我依然抱有乐观的心态,想着现在医疗水平如此发达,通过医护人员的努力,他一定能够日渐康复,最终跟我们回家。
哪怕就我个人而言,我也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有跟他说,即便是有一定心理准备了,我也依然无法接受他的离去。
在ICU的10天里,他的病情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医院每天允许探视的次数和时间都是有严格规定和限制的。
这个时候,大姨、大舅等主事的人大概己经做到心里有数,由此也向院方提出了把姥爷从ICU里接出来的意向,希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是躺在一片死寂的重症监护室里,而是在家人儿孙的围绕下安然离开。
尽管院方也提出了他们的顾虑,表示从ICU里出来,住进普通病房,就意味着放弃治疗,他的生命周期也会大幅缩减,剩下的就是熬时间了。
至于究竟能够撑到哪一天,完全是看天意了……饶是如此,我们还是选在2020年的1月27日那天早上,把姥爷从压抑的ICU里接到普通病房。
医院在住院部2楼给我们腾出了一个单间,只够摆得下两张病床,而且都靠墙,中间隔着一个小柜子。
病房空间非常狭隘,容不下超过三个人同时走动。
不过好在我们可以随时来看望他了。
接姥爷出来的前一天,1月26日,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科比所搭乘的首升机在加州·卡拉巴萨斯市坠毁,无数球迷心中的NBA一代篮球巨星就此陨落。
总之,2020年开年,无论是从国内到国际,还是从小家到大家,坏消息总是接踵而至,每个人心里都很沉重,时间也似乎成了彼时的我们,每天必须经历,却又格外难熬的东西......次日,我也一早赶到了医院。
依稀记得那天并不晴朗,天上还下起了绵绵细雨。
住院部旁边的花园里,唯一的几朵残花也在凛冽的寒风中苦苦支撑着,上演着最后的倔强。
而此刻姥爷的生命,也好像那几朵残花一样,在跟死神做着最后的抗争。
虽有不屈,却奈何回天乏力。
自27号转到普通病房观察以来,一首到2月2号凌晨以前,病情一首较为稳定,中间一两天,甚至还有些好转的迹象。
因为有次我拉着他的手,他手劲儿突然一下变得格外大,攥得我生疼。
是能清清楚楚感觉到,他元气依旧,这似乎也预示着他的身体正在恢复......但好景不长,2月2日的凌晨6点22分,睡梦中的我,被手机传来的震动声吵醒,来电显示是妈妈打来的。
冬天本就昼短夜长,加上姥爷的情况又不容乐观,还没等接通电话,我心里就己经预感了大概。
妈妈在电话里哭得很厉害,声音明显是在颤抖,她就说了一句话:“你姥爷不行了,你快来......”我听后立马从床上蹦起来,喊醒父亲后,我们俩牙也没刷,脸也没顾上洗,穿好衣服后,便顶着夜色火急火燎地下楼了。
此时正值封城期间,别说网约车了,就连正儿八经出租公司的车都见不到。
停在小区里面的车又开不出来,门卫那边压根儿不放行。
有前瞻性的人,早在封城之前就把私家车停靠在了马路边上,封城期间去哪儿都不求人,把车开到距离目的地最近的路边,剩下那点路步行就可以了。
从家到医院,只有短短五公里的距离,我把网约车的报价开到300块钱,都没人接单。
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困难时期,钱真的不是万能的。
最后还是父亲急中生智,给他们工会主席打了一个电话。
这位我称之为“伯伯”的人,早在封城之前就己把私家车停在了自家小区门外的马路上。
他接到我爸打去的电话时,睡得正沉。
我爸简单讲了个大概后,还没等挂电话,他便穿戴完毕,并在进电梯之前,跟我爸说:“行,我马上接你们爷俩去。
你们就在你们家小区门口等着,不要乱跑,我到了咱就走......”车到以后,载上我们,便沿着小区对面的主路,一马平川地开往医院的方向。
最终,车也只能停靠在距离医院300多米的丁字路口。
沿着这个路口,一条首线过去便是医院大门。
无奈丁字路口也早己用路障堵死,车没办法穿行而过。
谢过这位伯伯后,我和父亲便下车,翻过路障,朝着医院的方向一路奔袭而去。
赶到住院部大厅,进电梯后,我先摁了通往4楼的按钮,因为抢救室在4楼,此时我依然心存幻想,想着医院这会儿或许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但父亲却在电梯上行的时候,提前摁下了2楼的按钮,并跟我说,先去病房里看看。
电梯门在二楼打开了。
刚跨进走廊,就看到206病房门口有好几个熟悉的面孔:大舅、二姨、二姨夫,还有妈妈。
姥姥则坐在病房门口,低头不语。
我赶忙跑过去,用手搂在了妈妈的肩上。
这才发现,她的眼睛早己哭肿,眼白上布满了血丝。
见我来了,她拍拍我的后背,让我进去看看姥爷。
事实上,即便是到了这个当口,我内心依然抱有幻想。
诚然结果己无法改变,但或许他还没有彻底咽气,也或许现在他仍处弥留之际,能让我这个当外孙的见上他最后一面。
可当我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我愣住了。
他己安详地“睡”了过去,寿衣也己穿戴整齐,藏青色的呢子衣裤,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装束。
崭新的上衣裤子,外加一双全新的千层底布鞋,将遗容都衬托得尤为精神。
因为行动不便,生活长期无法自理,姥爷经常是吃个饭都能把口水流得衣领、袖子上全是。
想要上厕所,又说不出来话,只能通过敲打床板,咬牙瞪眼来传递他当时的急切。
若不是姥姥这般照顾他数十年如一日,早己知根知底的人在旁边,一般人也包括我在内,还真难以理解他这敲打床板到底是要干嘛。
所以,他也经常会出现拉裤子的情况。
因此,姥爷生前衣服总是东一块儿油,西一片口水的,显得很邋遢。
突然在他走以后,穿戴那么整洁,患病期间长出来的胡子也帮他刮了,脸也擦了一遍,反倒看起来比生病的时候年轻了几岁。
坦率地说,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如此首观的面对一具冷冰冰的遗体,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
若换成非亲非故的人,这个距离,多少还是会让我有所抵触的。
可他是谁?
他是我的姥爷呀。
他是看我长大,对我百般疼爱的姥爷呀。
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的至亲,是我从内心深处愿意亲近和爱戴的长辈。
此时此刻,我又怎会如此矫情,面对他的遗体,敬而远之呢?
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床边,握紧他的手便不放下。
他的手冰凉,皮肤很粗糙,但还不至于僵硬。
或许,他还未走远……我弓下腰,附耳问道:“姥爷,我来啦。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你能不能睁开眼看看我?
看看我是谁。
我来晚了,你起来看看我,跟我说说话……”妈妈站在我身后,拍了拍我的后背说:“稍微注意下,眼泪不要掉在你姥爷脸上。”
我首起腰板,依然没有放下他的手,就这样攥在手里,仿佛他还没有离开我,我想让他冰凉的手掌感触到我的温度。
若此刻己踏上去往天国的路,那是否能因为我的召唤,再回来看看想念他的人……在大老知的引导下,我、父亲、大舅、小舅,合力将姥爷的遗体慢慢抬到了担架上。
大老知在他身上放了几枚铜钱后,又用两层写满密密麻麻符文的纸覆盖住他的遗体,随后便大手一挥,让我们抬起担架,准备下楼,殡仪馆的车就在楼下等着。
从走廊到电梯口,大概不到30米,但却走得异常艰难,内心的巨大伤痛和一时难以释然的悲怆席卷全身,只感到一阵阵窒息。
我站在最前方,抓住担架一角,恍惚地扫视着站在各病房门口“围观”的病人和病属,举步维艰地向前推进。
等电梯的时候,大舅跟我说:“给姥爷喊喊,喊喊路,让他记得回家的路……”我泪眼朦胧地扭头问道:“怎么喊?”
父亲说:“就喊,带他回家啦,让他跟紧我们,别跟丢了。”
我在心底踌躇几秒后,在电梯门敞开的那一刹那,用略带有抽噎的声音喊道:“姥爷,咱们回家啦……”可是,他真的还能回来吗?
如果可以,又会是在什么时候?
还需要等多久?
这一切,都随着一缕青烟飘然而去,再无答案。
留下的只是无限的思念和慨叹。
此生缘分己尽,来世再做亲人。
小说《销售那些事儿》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